Thomas Demand:虚拟的真实
ART & CULTURE PHOTOGRAPHY | 9月 27, 2021

Thomas Demand
当一件摄影作品挂在墙上时,它必须具备所有的交流功能,完全独立地传达意义,和观众交流,艺术家不能添加任何解释。
I
托马斯·迪曼德 (Thomas Demand)
托马斯是一位出生于德国的雕塑家和摄影师,现在在柏林和洛杉矶两地生活。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自1992年起,在MOMA、Tate、古根海姆博物馆、新德国国家美术馆、加拿大国家美术馆、圣保罗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悉尼双年展等国际重要展会上的频繁亮相,让他成为最有国际声誉的当代艺术家。他按照比例,以令人惊叹的细节和准确性,用纸重建了时事中的著名场景,然后对它们进行拍照。

Thomas Demand
从面相上看,托马斯·迪曼德(Thomas Demand)长了一张敏感而焦虑的脸,从经历上看,绝对的生逢其时,1964年生于慕尼黑,26岁之前在慕尼黑艺术学院学习雕塑、1990年到1992年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虽然没有直接师从摄影界如日中天的贝歇夫妇,但是从日后的创作来看深受其影响,尤其是“贝歇风格”的摄影经过托马斯·施特鲁特(Thomas Struth)、托马斯·鲁夫(Thomas Ruff)、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等几位高徒薪火相传,从90年代开始,屡创摄影作品的天价记录,在摄影理念上也拓展为一种艺术观、方法论。
托马斯·迪曼德从雕塑家入行摄影,厚积薄发,终于当仁不让地成了新一代的接班人。批评家特里·斯密斯(Terry Smith)认为迪曼德作品中那看上去冰冷的视觉感受,是“无表情外观”美学的拓展,故命名其为“后贝歇风格”的作品。

Thomas Demand
他的职业生涯是从雕塑家开始的。但在1993年,他的实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再为了记录自己的雕塑拍摄照片,而纯粹为了拍摄照片制作雕塑。现在,他的实践变成了探索摄影作为一种媒介的意义,以及图像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通过缜密的工艺,他的作品用幻觉触发观者心中的认知,不管是残破的厨房(萨达姆·侯赛因被捕前在那里吃了最后一餐),亦或是浴缸的角落(德国政治家乌韦·巴舍尔被发现死亡的浴室)。


然而,托马斯不是一个幻想家,他的作品里没有技巧。相反,他提出了一个“现实总是在变化的”观念,挑战客观真理的概念。他的作品是对现实世界的模拟,完全是主观的,将“我们如何重建记忆”进行了可视化。


托马斯·迪曼德用摄影的形式与现实世界进行博弈,然而,他又明智的与摄影和现实之间保持着合适的距离。他作品中的形象,主要是室内的景物与陈设的静物。这些形象都是用彩色纸板精心制作的实体模型。他精彩的作品“格罗特 (Grotte) 2006” 据说整整制作了两年的时间。
迪曼德并不把自己当成一个摄影家,将他所运用的创作方式作为一种对现实世界翻译转换的模式,或者是上演对现实物体进行复制的过程。他也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模型制作者,因为这些模型仅仅是对现实形象的暗示,它们并不被展出,并且在拍摄照片之后,它们都会被毁掉。他曾经销毁了一件用了3年创作的作品。



然而,对真实物体的“模仿”成为迪曼德作品中摄影与模型制作两者之间的关联之处。并且,这种模仿的再现使观者的注目产生了游离。迪曼德提出,“照片提供了你需要确切观看的形象信息,而随后,这些形象信息就在你的眼前解体分离了。”


他着意强调这种通过暗指公共的形象,或复制模仿被媒体已广为传播,并且在我们的视觉意识里已经根深蒂固的众所周知的犯罪现场或重大事件的新闻图片的做法与现实之间建立的关系的脆弱性。


这些通常与实物比例为1:1的仿制模型,通过去除原物体表面的细节而只注重原物体的物质本身的方式,对仿制原形进行了简化与提取。
在迪曼德的作品中,人的出现仅仅是作为留下的踪迹,当他的作品涉及当前的事件时,这一特点变得尤为强烈。如作品“克劳斯 (Klaus) 2006”,仿制了一个占据德国媒体数周的具有悬疑的虐待儿童事件的现场。“大使馆 (Embassy) 2007”展现了被洗劫的尼日尔驻罗马大使馆的场景。在这里,中央情报局为伊拉克战争辩护的文件被偷走。
迪曼德的摄影图片激活了被大众媒体编译了的图像记忆,并且同时与这些图像创造性的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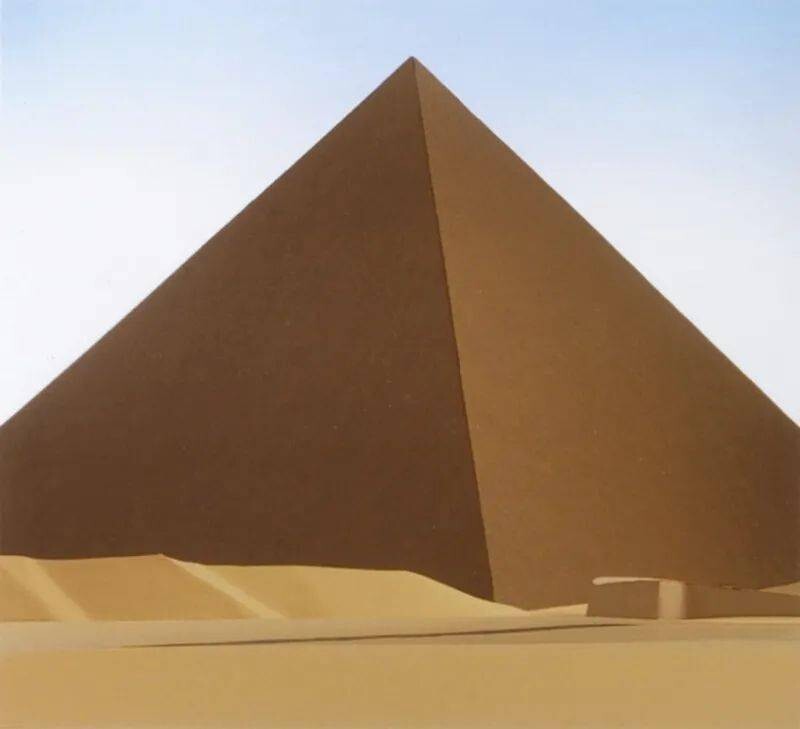


“物” 的气息一直是托马斯·迪曼德照片最大的特点,一种真实的存在感兼并一种超现实的气息。托马斯·迪曼德追求 “物” 的私有化及陌生化,尝试为各种被人们已定义的物件作身份消除,同时将摄影和影像与装置的界限进一步打破,独具一格的摄影作品使他成为上个世纪末最耀眼的摄影师之一。



II
一些具体的作品分析

托马斯·迪曼德, 《档案室》, 1995
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1995年的《档案室(1995)》(”Archive”)和1996年的《办公室(1996)》(“Office”)。《档案室》这件作品呈现了一个空空的房间里,那是纳粹政权在20世纪30年代的档案室,图片中那数不清的灰色盒子,每一个盒子里都有一个人的档案,极权政府对大众的无形的控制,就在这个办公室里转化成可以看得见的材料。
接下来的历史,大家都耳熟能详,纳粹政府铁桶一般统治着德国,大屠杀和销毁档案一样变得迅速而彻底。请注意画面中的一尘不染、纯净的气氛,似乎是在暗示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美化纳粹制度的手法。乍一看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在了解到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之后,作品所暗示的力量就峥嵘毕现了。所有的盒子都是统一的尺寸、色泽,每一个都对应着一个人的身份。这个单调而冰冷的场景唤起历史深处的记忆和无法抹去的罪证。

从左到右: 发表在报纸上的《档案室》的原始照片,托马斯·迪曼德, 《档案室》, 1995
再说《办公室(1996)》(“Office”),那张画面上警察局的档案散落一地的作品,那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另一个极权制度下的安全机构——东德秘密警察总部,被洗劫之后一片狼藉的场景。所有的散落的秘密档案都有人身控制和政治阴谋的象征,与干净冰冷的气氛匹配出不可思议的怪异感。这些作品展示了特定空间中特定的实体对象,由于缺少人的痕迹,熟悉的场景,又惊人的冷漠,当它们就这样展示给我们时,我们的感觉是给机器人参观的展览。
朗西埃评价作品道:“这些图像的转换产生了异感,与媒体的图片产生了距离,与现实也产生了距离,观众在这个距离中重新思考历史和政治”。档案在社会统治之中,扮演什么角色?档案、身份、个人、体制的关系是什么?放之于历史和政治事件中呢?
迪曼德的作品最为直接地继承了新客观美学的视觉体现,然而完全不是为了传达真实、事件和在场,也不是单单作为艺术家对监控的社会的一种反映,而是更加深层地思考媒体、控制、犯罪交织在一起的现实,有趣的是观众的关注点从图像转移到了事件,进而是事件的图像,而事件本身是政治的。超越了事件本身,把观众带到对现实思考,这些事件又是高度政治的,犯罪的。

从左到右: 《大使馆系列-1》 /《大使馆系列-2》/《大使馆系列-3》/《大使馆系列-4》, 2007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用“档案”取代了“认识”,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的管理对档案的依赖,档案就是“权力、实践、制度”的联结,是“高度差异化的命题的形成和转化总系统”;换句话说,我们处在“档案社会”的牢笼之中而不自知。
迪曼德在诸多作品中显露出他对档案的兴趣,除了《办公室》和《档案室》。还有《大使馆(2007)》(“Embassy”) ,展现了被洗劫的尼日尔驻罗马大使馆的场景。在这里,中央情报局为伊拉克战争辩护的文件被偷走。有意思的是这个系列用了7张照片展现,如同侦察现场,从不同的角度取证,观众在展厅里走向作品的同时,从挂着国旗的远景中的房舍,穿越空无一人的走廊,走到了虚掩的门前,再进入凌乱的办公室,去采集又一件政治阴谋的证据。

从左到右: 托马斯·迪曼德, 《演讲台》, 2000 ;《谋划》, 2005

从左到右: 托马斯·迪曼德, 《克劳斯讲台系列-6》, 《克劳斯讲台系列-2》, 2006
迪曼德的作品的命名常常没有提示性的信息,而且画面呈现的场景也及其平常。但实际上都是政治和犯罪的发生地,比如《演讲台(2000)》(“Podium”)是塞尔维亚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萨夫列维奇(Slobodan Milosavljevic)在1989年6月28日在Gazimestan演讲的演讲台。
《谋划(2005)》( “In Attempt “)呈现的工作室则是属于艺术家和恐怖分子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Baader-Meinhof),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策划针对国家公诉人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下议院爆炸事件而声名狼藉;《 厨房(2004)》(“Kitchen”)的图片来自于士兵的快照,图片中的厨房是萨达姆·侯赛因最后的藏身之处——提克里特(Tikrit,在巴格达的北部,萨达姆的故乡)。《克劳斯(2006)》(“Klaus”),仿制了一个占据德国媒体数周的具有悬疑的虐待儿童事件的现场。

从左到右: 1937年,施佩尔(右)向希特勒展示巴黎世博会德国馆模型, 《模型系列-2》, 2000
最后说说媒体津津乐道的迪曼德技法。迪曼德在大众媒体上得到图像资源,再用纸模还原成实际尺寸的场景,拍摄完成后,纸模型销毁。再一次采访中,迪曼德坦言纸模的创意来自于希特勒在1937年检查巴黎世博会德国馆的模型的照片(如上图所示),让他觉得模型能创造“真实”,又是脱离了现实的真实,也独立于媒体照片的对“真实的呈现”,它完全独立于事件之外。另外“纸模的摄影不同于绘画也不同于雕塑,最后介于两者之间,观众的视觉经验之外的一种东西”(迪曼德)。这样,这些摄影就将“报纸摄影转换成了剧院场景,没有人物和词语的戏剧场景。这种双重转换建立了一种距离感,要求观者自问,如果我们不被告知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光看这些照片,我们回看到什么?什么是事件?什么是一个事件的图像?是什么使一个地点指明事件的在场?”(朗西埃)。
他的作品激活了被大众媒体编译了的图像记忆,并且同时与这些图像创造性的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进而使观众有空间进行历史层面的思考,再次审视现实;当他的作品涉及当前的事件时,这一特点变得尤为强烈。另一方面,在迪曼德的作品中,人的出现仅仅是作为留下的踪迹,政治犯罪现场中人的缺席可以理解为制度的犯罪,而非个人的,而历史中的制度犯罪又常常是以正义的名义,从绑架大众意志中获取支持,以篡改历史作为手段的,迪曼德从历史的尘封中,从大众回忆的深处,重新造访历史现场,提供一个无言的立场,换取观众自觉的思考,这一点尤为值得回味。
III
托马斯·德曼德的日常
以下由美国知名艺术批评家、艺术史家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1955年—)撰写,李鑫翻译。哈尔·福斯特的批评领域极其广泛,在艺术圈十分活跃,且著述颇丰,其代表作为《实在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al)、《设计之罪》(Design and Crime)等。

Thomas Demand
先从托马斯·德曼德的作品标题《日报》(The Dailies,2008年—)开始,它是日常生活场景中随处可见之物的iPhone快照,共二十余张,比如,沙砾中熄灭的烟头、洗衣机中的有色织物。报纸曾被称为“日报”,正如前一天的电影镜头,它们以资料的身份暗示短暂与迅速,但《日报》与之不同。
德曼德先敏捷地拍照,后慎重思考、严格挑选,他在每张照片的建构过程(制作纸张、纸板模型,将之拍下,最后选择特殊的转染工艺)中倾注心血。(他说过,“每输出一张照片,需40个小时。”)[2]因此,《日报》体现了不同的时间顺序和注意力,于是,它们提出一个问题:智能手机的图像指令系统能创作艺术吗?对于如此节制的主题,问题的措辞似乎过于宏大,但节制与宏大常在立意远大的作品中完美结合。[3]此外,平凡无奇的照片再次引发“何为艺术摄影之内容”的重要争论。
毫无疑问,《日报》是德曼德创作的转变。之前,他的许多图像基于重大事件的媒体报道,比如,德国政客或英国公主之死,此类图像可统称为“历史照”(The Histories)。不过,“历史照”往往语焉不详,因为多数细节被掩盖了,以致每处细节似乎都是线索,但《日报》一目了然。德曼德轻描淡写地解释道,“它们是同一位作者,只不过形式不同。”[4]我们可视之从高级别的类型(“历史照”意味着最高级别的历史画)转为低级别的图像制作(《日报》的多数照片是室内场景,且几乎可当作静物画)。在此,这只是德曼德将摄影与绘画相互联系的一种方式。

《日报3》

《日报13》
如同多数静物画,其关注点是触手可及之物,比如,《日报3》中浴室镜子下的梳子,《日报13》中早餐桌上的两个咖啡碟,这些是我们试图触及空间的图像。当然,我们触碰不到,不仅因为它们是艺术品,还在于图像中没有可触摸的事物(模型替代了指示物,二者不复存在)。静物画时常代表触觉含义与视觉距离之间的张力,而且,它偶尔在社交物品(比如,食物)与冷漠拒绝(不能吃的食物)之间产生矛盾。[5]这两类模糊性在《日报》中十分明显,并因建构主题本体论上的模糊性而得到强化。
在多数静物画中,物体位于中心,或可直接见到。《日报》却不然,它们通常呈一定的角度,仿佛从上方瞥见,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每天假装游荡、实则暗中观察的艺术家。不过,这些事物经常在室内:创作《日报》时,德曼德主要待在公寓、办公室或酒店。事实上,除了几乎不存在的自然,《日报》中的日常环境也受到严格控制,它几乎全由人造物与变性空间的“第二天性”组成。[6]在照片中,抽象往往意味着异化,至于这点,《日报12》中匿名酒店门锁处空白的红字“DON’T DISTURB”(请勿打扰)让人不寒而栗。正如《日报14》中结霜的窗户、《日报16》中被百叶窗遮住的窗户、《日报19》中既刺眼又混乱的栅栏,它们是窗户的图像。看见的事物遮住了背后的景色。[7]

《日报12》

《日报14》

《日报19》
镜子与窗户
斯韦特兰娜·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在其经典著述《描绘的艺术》(The Art of Describing,1983年)中阐述了17世纪荷兰绘画中的静物与室内陈设,并提出当时两种再现模式之间的明显对立。第一种模式是占主导地位的南方风格,即图像是透视世界的窗口,阿尔珀斯将之归功于阿尔贝蒂(Alberti);第二种模式是处于附属地位的北方风格,即图像是映射世界的镜子,她将之与开普勒(Kepler)相联。[8]阿尔珀斯解释道,前者侧重于观看者(“我看见世界”),后者集中在被看物(“世界被我看见”)。
此外,前者认为,世界因施令的观看者而存在,后者则假设,再现乃至观看者可能根本不存在,世界似乎仅以图像的形式存在。对于阿尔珀斯,二者并非一定对立;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与路易·马兰(Louis Marin)将之当作“传统再现”伟大成果的补充物,对于福柯,它体现在委拉斯凯兹(Velázquez)的《宫娥》(Las Meninas,1656年)中,对于马兰,则是普桑(Poussin)的《阿尔卡迪的牧人》(Et in Arcadia Ego,1655年)。在意大利与荷兰之间,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与法国画家普桑均参与了这两类绘画。[9]

委拉斯凯兹,《宫娥》,1656年

普桑,《阿尔卡迪的牧人》,1655年
德曼德也在《日报》中运用了这两种形式:除了照片中的镜子与窗户,还有由两种模式(“我看见世界”与“世界被我看见”)担保的处于内在紧张状态的两个装置——窗户被遮挡、镜子反射很少的物体,诸如此类。[10][德曼德还使用了既非镜子、亦非窗户的再现表面,比如《日报8》中的布告牌,它让人想起威廉·哈尼特(William Harnett)、约翰·皮托(John Peto)等人错视画中的类似装置,这是他将摄影与绘画相互联系的另一种方式。]阿尔珀斯将摄影与北方画派相联,照片是世界的直接印记这一共识亦支持此类艺术史分支,但德曼德一直试图将媒介的指示性解释变得复杂。[11]
我们知道,即便《日报》中的事物很常见,但最后的图像经过反复构建。它们不仅是观看对象,还是极活跃的艺术家——他拍照,挑选图像,建立模型,确定视角、灯光环境,构思画面,决定输出。虽然德曼德的照片中毫无人迹,但他隐匿在任何地方。事实上,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认为,它们是“纯粹的艺术意图”的手工品。[12]

《日报8》
事故与疏忽
在《日报》中,德曼德将这一清晰的阐述置于真实的压力下。当然,它们用看似偶然或事故的场景验证“纯粹的艺术意图”,比如,《日报1》墙上脱落的电源插座,《日报5》中廉价天花板上掉下的四块嵌板,《日报7》中被灰色格栅夹住的绿色纸巾,不一而足。“偶然”或“事故”的根源是坠落,重力在《日报11》(俯视棕色木甲板上的绿色枫树种子)等照片中显而易见。[13]
《日报》中另一个与之相反的特征是悬浮状态,比如《日报17》中穿过蓝天的晾衣绳上的五个别针。其他图像则体现两种状态之间的极度不平衡,比如,《日报20》中盛有胆汁的塑料玻璃杯在窗台上摇摇欲坠,《日报21》中处于白色浴缸危险边缘的橙色肥皂。[14]于是,在事故尚未发生时,它暗示了某种疏忽,它再次给弥漫作品中的意图性施加压力。在这一系列中,德曼德似乎将视线转向场景,同时又远离它们(“疏忽”的拉丁语意为“转向”)。也许,照片中的世界并不像最初那般井然有序。

《日报20》

《日报21》
德曼德也用其他方式强调照片中的超构图本质,比如,《日报2》中相对随意的烟头,《日报8》中抽象的布告牌。《日报5》中脱落的嵌板、《日报11》地上的种子让人想起先锋派的即兴策略,它们回应了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与汉斯·阿尔普(Hans Arp)的著名实验,如《三次标准的终止》(3 Standard Stoppages,1913—1914年)与《依据机遇法则排列的正方形》(Squares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Chance,1917年)。
简言之,德曼德以非构图的形式反对构图,因而,这组矛盾的照片看似既深思熟虑、又武断随意,但它与随机不是一回事。鉴于《日报》,20世纪的机遇策略突然比即兴策略更武断(毕竟,裁决人即决定者),意图性与不确定性不再对立。
于是,《日报》借由这一融合打破摄影与绘画之间的传统假设。19世纪摄影话语的核心是艺术与自动主义之间的冲突,它认为,摄影若要成为艺术,则不能过于依赖机械化与偶然的机遇。但在《日报》中,与自动主义的双重关系既是阶段性的、又是短暂的。[15]抽象与再现之间的对立在现代主义绘画的话语中同等重要,只不过二者同时出现,《日报》也厌恶传统的二元对立。

《日报2》

《日报5》
细节与仿品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其极具影响力的文章《真实效应》(L’effet de réel,1968年)中谈论了细节在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中的作用,他分别选择了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与米什莱(Jules Michelet)的文章。巴特认为,在叙事中,一切均有所意指,似乎无所指代的偶然细节也是如此,因为它所表现之物无足轻重,只是偶然世界微不足道的事实,从而帮助作者塑造真实的印象。[16]当照片与世界发生指示性关联时(对于媒介,这种情况通常是必需的,甚至自然而然),它在本质上指涉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仅产生“真实效应”的细节。
在德曼德不完美的模型中,他不但没有切断摄影与现实之间的传统纽带,反而将之延伸。如同其他照片,《日报》仅带来图型的幻觉,因为图片中的建构与真实事物之间的差异日渐明晰。在弗雷德看来,这才是本质,于是,图像能够记录“纯粹的艺术意图”,因为它们仅包含德曼德需要的细节。不过,它无法解释为何某些细节包含在内,某些却没有。
德曼德将《日报》比作俳句,它在某种程度上暗示描述性细节,诚然,许多图像具有诗意的简洁。[17]试举一例,《日报11》中棕色木甲板上的绿色种子让人联想到受俳句启发的意象派诗歌,比如,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最出名的诗句:“人群中这些面容的忽现/湿巴巴的黑树丫上的花瓣”(《在地铁站》),以及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那么多都要依赖/于/一辆红色独轮/车/它浇透了雨/水/挨着一群白色的/鸡”(《红色独轮车》)。[18]
《日报》中的某些照片由此忽现(对于我,《日报17》晾衣绳上彩色别针的舞蹈就是如此),这一特质让我们思考此类经验的现状。正如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在150年前对现代艺术家的首次责难:短暂还能触及永恒吗?(至于“现代性”,他的名句是,“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9]更慎重而言,在井然有序的世界中,日常事物还能使人顿悟吗?意象派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正值技术变革的密集时期(常称之“第二次工业革命”),它准确地强调知觉,因为日渐增加的调解会威胁知觉。类似俄国形式主义、现象学哲学,印象派诗歌试图突破人的感知,反对兴起的第二天性。因此,一个世纪后,德曼德在《日报》中如法炮制,但最不同之处在于,他接受调解后的世界,并从中汲取灵感。

《日报11》

《日报17》
对于德曼德,他的照片也与感知相关。他说过,“我的雕塑只是仿品,它们由可识别的、数量精准的符号制成。”[20]因此,他的细节不仅强调图像的制作,更重要的是,还作为观看、阅读、回忆的测试而激活它们。(在此,仿品是暗示性术语,它不仅要求我们为他的照片命名,还要念出它们。)分散的注意力是“新闻的真正状态”,德曼德如此解释“历史照”,但这也适合《日报》。他继续说道,“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事件的传播在媒体上留下的模糊痕迹”。一方面,他相信,分散的注意力会带来“无处不在的弥漫感”;另一方面,它让事件的“模糊痕迹留在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中”。那些模糊痕迹是由照片中迟钝的细节唤醒的吗?当然,作品的深层主题是我们共同的媒介记忆,《日报》也指出深藏于日常琐事中的记忆维度。
“模糊痕迹”是些许矛盾的说辞,但它有用。为了有说服力,细节(即巴特意义上的刺点)不需要准确。比如,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与格哈特·里希特(Gerhard Richter)作品中具有创伤力量的模糊痕迹,它也存在于德曼德的作品中。[21]不仅症状存留在细节中,死亡也常常如此:小事往往会致命。在《伊凡·伊里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ich,1886年)中,托尔斯泰(Tolstoy)如此引导他的主人公,正如伊里奇痛苦地注视着肿块变成残酷的敌人——监视他,跟踪他,最后带走他。他称这种平凡、终有一死之物为“它”。我在浏览《日报》时会发现此类迹象,比如,它会出现在《日报20》褪色的水中吗?

《日报7》

《日报15》
凝视与刺点
艺术家可以凝视,观者亦然,但《日报》中还存在其他的凝视。有时,某一细节、某个事物、作为整体的照片似乎回头凝视我们。[22]这不仅是“我看见世界”与“世界被我看见”之间的竞争,还有“我看见它”被“它看见我”困扰。我们说“它吸引我的视线”是何意,正如《日报13》咖啡碟中的椭圆形橡皮筋吸引我们的视线?什么赋予特定细节以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到底在哪里?细节、观者还是同时存在于两者中?这种对视觉的捕捉体现在《日报7》中灰色格栅中的绿色纸巾、《日报15》中铁丝网上的棕色杯子:它被网捕获,进而轮流捕捉我们的凝视。
诺曼·布列逊(Norman Bryson)在一篇论静物画的文章《注意被忽视的事物》(Looking at the Overlooked,1990年)中解释了“被忽视”的双重含义。在静物画中,对象往往是次要、被忽视的事物,但其描绘方式往往让我们过度关注,于是,我们有时以近乎美杜莎式的强度忽视它们。[23]同样,我们的凝视留在细节上,这是其力量的体现方式。这种力量也可能带来威胁的暗示,即,它会威胁我们的视觉。
英语单词“detail”(细节)源自法语动词,意为“切断”,而且,自弗洛伊德(Freud)以来的精神分析学家已经发现,失明的恐惧与阉割的威胁之间存在精神上的联系。[24]拉康(Lacan)认为,世界上存在普遍凝视,它先于主体而存在,因而,主体认为它是一种威胁。他在《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1973年)中提出,凝视“象征阉割现象中的核心缺失”。[25]这一创伤凝视的概念影响了巴特,因而,他在《明室》(Camera Lucida,1980年)中提出刺点概念,即,照片中出乎意料的细节不仅吸引我们,还会刺透心灵。
巴特认为,刺点并非摄影师有意为之,它只是观者的偶然体验。但在德曼德的照片中,我们面临刺点的悖论,即,若非总是刻意的,也不全属偶然。[26]当然,在我看来,《日报》中的某些细节是“刺点”(我提过《日报13》中的橡皮筋),它接近美杜莎的视角(《日报2》沙盆中的烟头具有这种力量)。同时,模型与照片的平滑表面会柔化我们的视线,正如拉尔夫·鲁戈夫(Ralph Rugoff)所说,德曼德的图像“似乎用平静的秩序和寂静迎接我们的凝视”。[27]对于拉康,如果某些照片会欺骗眼睛、产生错视感,那可以说,几近所有图像的目的是驯服凝视。《日报》在不同的时刻激活了三种观看类型:视觉的欺骗、野性以及驯服。[28]

《日报18》

《日报1》
巧计与顽固
《日报》是视觉概述,但它们时常会产生似曾相识感,这种新鲜与熟悉的矛盾结合是德曼德的典型特征。在一次不同寻常的对话中,德曼德告诉亚历山大·克卢格(Alexander Kluge),“我脑海中的图像,有些十分平庸,其他则意义甚多,但实际上,它们都是我知道的事物。”我们也知道它们,或者他以为我们知道。部分原因在于,德曼德用已有的再现(比如,新闻照片、明信片与手机快照)建构图像。
不过,这种叠加不是后现代主义者对现实的批判。德曼德将摄影对世界的调解当作既成物,他假设我们也应如此;他的项目不是为了揭秘现实,而是重新塑造、重新想象现实。于是,他的艺术代表了再现与指示物之间感知关系的文化转移,其中,指示性与建构性之间的古老对立不再紧密相联。在由摄影图像与人造图像组成的世界中,媒介的指示性特征不会自动超过其他方面。我们不再猜测摄影图像的真实价值,我们警惕它的虚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新现实主义应运而生,它用巧计使现实再次变得真实,亦即,变得理智、可信、简单有效,诸如此类。在服务现实的新艺术巧计方面,德曼德是关键人物。[29]
这一巧计使他的照片领先我们,甚至抢先我们,反过来,他向我们灌输“顽固”。这一术语由克卢格在《历史与顽固》(History and Obstinacy,2008年)中提出,意即,存留在“历史底层”之物的顽固性。[30]克卢格评论道,德曼德的“图像中全是人的缺席。”他不仅仅指,照片中没有人,相反,他意指其他人的矛盾存在(他们不在场,却留下踪迹)。“不存在空无的空荡”,克卢格继续说,“在我看来,漩涡是图像中的关键媒介。”这一评论是神秘的,但吸引克卢格的在场与缺席不仅是已有的再现,还是先前之人留下的活动,它再次顽固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日常家具中。这只是《日报》的细节,是“死亡劳动的残留物”,克卢格也如此评论。这会是思考作品中“模糊痕迹”的另一种方式吗?这是实现“纯粹的艺术意图”之外的另一种方式吗?
克卢格继续说道,“图像出现在”第二天性中,其中,所有的事物都是人造的,“人的能力”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外面,并面对我们”。于是,德曼德图像的“媒介”试图重新复活“死亡劳动的残留物”、激发第二天性、重获被异化的“能力”,至少这个项目是如此的。事实上,它是不易实现的乌托邦,但他的图像由此发挥“空无”与“漩涡”的作用。在此,“媒介”涉及它的古老含义,也就是与死者接触的形式。
克卢格与德曼德还讨论了“第三天性”,他们不仅指由人造物、机械制造物组成的世界,还有不受人类掌控、由结构、系统、网络驱动的世界。“如果公共领域、艺术、人际关系不再随着社会的复杂性而增长,”克卢格提醒我们,“那么,第三天性将由此产生。”不过,这是克卢格相信德曼德等艺术家能够干涉的地方:“你的全部作品的核心”集中在“人们在第一天性、第二天性、第三天性之间摇摆的方式。”但在艺术实践的层面,这究竟意味什么?[31]

《日报9》

《日报10》
不妨看看《日报》中的物品,比如,《日报9》中松散的橙色围栏,或者《日报10》中更衣室的俗气凳子。它们是资本主义垃圾空间的材料,极像人造物、非常异化,以至于几乎是后人类的。[32]鲜有人知道它们是如何制造的,但它们每天被多数人使用。在《日报》中,它们更像被人用过,它们损坏了,比如《日报1》中的电源插座,或《日报18》中被丢弃的饮料。然而,矛盾之处在于,使用、破坏、垃圾让它们再次变成人类,至少,它们留有消费的痕迹,即便不被我们使用。这正是德曼德介入“有组织的修补”之处,这是他描述挑选、建模、拍摄日常事物的方式。如果对世界的调解理解成抵抗压在我们身上的第二天性、第三天性,那么“事物必须放慢速度,”德曼德说道。
“我们看见历史留下的幽灵,”克卢格如此评论德曼德,“它像幽灵,却是现实。”不过,德曼德展现已有再现之踪迹、死亡劳动的存留物的方式不单是神秘的。同样,他试图激发记忆维度层面的认知:“铃声会在长期记忆中响起。”矛盾的是,这种记忆维度带有投射效果,它是未来的向量、含伦理成分的向量。《日报》向我们呈现的生活素材,通常是庸俗的、琐碎的、让人厌倦的,甚至是致命的。但,美也蕴含其中。它不是救赎,但可能是忽现,甚或是顿悟。
注释:
[1] 译自October 158, Fall 2016, pp. 100–112.
[2] 在转染过程中,有三种印刷矩阵(即三种不同的原色),明胶用于定色,其色调范围高于任一种技术。伊士曼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于1994年停止生产这一工艺的原材料,仅少数印刷商继续生产所需的设备,且具备专业知识。德曼德在《托马斯·德曼德:日报》(Thomas Demand: The Dailies,2012年)中解释了《日报》的创作过程。本文的首版发表于《托马斯·德曼德,日报》(Thomas Demand, The Dailies,2015年),感谢乔治·贝克(George Baker)为此次修订提出的建议。
[3] 由此观之,《日报18》(没有杯子的瓶盖与吸管)即为一例。人行道上,垃圾遍地,它斜躺着,形如被丢弃的陀螺,但随着映射于地面上半椭圆形阴影的旋转,这个小陀螺投射出一个行星系统。
[4] 参阅Coline Milliard, “Same Author, Different Form,” Artinfo UK, April 18, 2012. “历史照”中已然隐含这一观点:日常生活的微末之物与官方历史的重大事件共同存在。
[5] 关于这一点,可详见Norman Bryson, Looking at the Overlooked: Four Essays on Still Life Paint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6] 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在写于1914—1915年的《小说理论》(The Theory of the Novel)中讨论了“第二天性”,在他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家们也讨论过。我将在后文回到这一点。
[7] 德曼德将照片压在树脂玻璃下方,并将其安装在无框铝上,亦即,他将照片当作对象而呈现。
[8] 详见Svetlana Alpers, The Art of Describing: 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9] 详见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Pantheon, 1970); Louis Marin, “Toward a Reading of the Visual Arts,” in The Reader in the Text: Essays on Audience and Interpretation, ed. Susan R. Suleiman and Inge Crosm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Svetlana Alpers, “Interpret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or, The Viewing of Las Meninas,” Representations 1 (Winter 1983); and Craig Owens, “Representation, Appropriation, and Power,” Art in America 70, no. 5 (May 1982). 在此,我仍然同意克雷格·欧文斯(Craig Owens)的观点,他与阿尔珀斯、迈克尔·弗雷德的争执是后现代主义兴起期间艺术史、艺术批评之间紧张关系的生动案例。
[10] 在阿尔珀斯的地图中,镜子与窗户之间的对立可以延伸至迈克尔·弗雷德的专注性与剧场性之间的对立,(正如我们所见)弗雷德是德曼德的大力倡导者。但这两种模式忽略了德曼德是如何混淆此类二元对立的。
[11] 对于摄影话语中范式的持久性,可参见John Szarkowski, Mirrors and Windows: American Photography Since 1960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78).
[12] 参见Michael Fried, Why Photography Matters as Never Befo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71. 类似绘画,摄影体现了不同于雕塑的一个优势,也是年轻的波德莱尔在1846年沙龙中认为雕塑“使人厌倦”的原因。弗雷德与德曼德均引用了这一观点。
[13] 后来,《日报》中又增加了一张照片,即一堆信件从邮筒中掉落。对于不在场的收信人,这是偶然事件。
[14] 重力与悬浮状态是身体与照片协商的结果,这种分担可能会强调德曼德在此引发二者之间的微妙同情。
[15] 对这些问题的精彩解释,可参见Robin Kelsey, Photography and the Art of Ch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6] 参见Roland Barthes, “The Reality Effect” (1968), in 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6). 巴特写道,“从符号学角度而言,‘具体细节’由指示物、能指直接组成;所指被符号排除,当然,也有可能形成所指的形式,比如,叙事结构。”(第147页)
此处,细节几乎妨碍了意义的产生,这一对立不仅与“世界被我看见”与“我看见世界”之间的对立相关,而且,也与卢卡奇用以区分自然主义小说(他对此深感遗憾)与现实主义小说(他支持现实主义小说,因为它涉及对社会的叙事解读)之间的描述与叙事相关。在这种意义上,德曼德更像一名现实主义者,而非自然主义者。
[17] 参见Demand in Milliard, “Same Author, Different Form.”
[18] 参见Ezra Pound,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1913);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Red Wheelbarrow” (1923).
[19] 引自Charles Baudelaire,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1863), in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 trans. and ed. Jonathan Mayne (London: Phaidon, 1964), p. 13.
[20] 参见“A Conversation Between Alexander Kluge and Thomas Demand,” in Thomas Demand (London: Serpentine Gallery, 2006), pp. 51–112.除非另作说明,关于德曼德与克卢格的引用均出自这篇文章。
[21]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我的另一篇文章The First Pop Age: Painting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Art of Hamilton,
Lichtenstein, Warhol, Richter, and Rusch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正如德曼德在其他场合所说,“刺点”并不与平庸相对。
[22] 参见Andreas Ruby, “Memoryscapes,” Parkett 62 (2001). 拉尔夫·鲁戈夫写道,“似乎有东西在盯着我们,那些黑洞没有映射我们的凝视,而是祈求主观上的盲点。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唤起‘超越’——欲望不断地传播。”参见Ralph Rugoff, “Instructions for Escape,” in Thomas Demand: Phototropy (Bregenz: Kunsthaus Bregenz, 2004). 对于我,这种“超越”与死亡相关,而不是欲望。
[23] 参见Norman Bryson, Looking at the Overlooked: Four Essays on Still Life Paint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1990).
[24] 详见Sigmund Freud, “Medusa’s Head” (1922).
[25] 引自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W.W. Norton, 1978), p. 77.
[26] 参见Walter Benn Michaels, “Photographs and Fossils,” in Photography Theory, ed. James Elki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27] 参见Ralph Rugoff, “Instructions for Escape,” n.p.
[28] 拉康认为凝视是邪恶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则认为它是善良的,至少,他认为光晕能够让物体回到我们的凝视。在德曼德的作品中,视觉欺骗无处不在,比如,《日报19》中的野性,《日报14》中的驯服。
[29] 这种巧计通常是重构的形式,一直旨在实现事件的重复,无论是历史的或想象的,它在当代艺术、行为艺术、小说以及其他形式中普遍存在。对于我,典型例子是本·勒纳(Ben Lerner)的小说《10:04》(2014年)、塔西塔·迪恩(Tacita Dean)的电影《舞台事件》(Event for a Stage,2015年)。关于我对这一策略的缺陷的评论,可参见“In Praise of Actuality,” in Bad New Days: Art, Criticism, Emergency (New York: Verso, 2015).
[30] 参见Alexander Kluge and Oskar Negt, History & Obstinacy, ed. Devin Fore (New York: Zone, 2014). 在克卢格精彩的导言中,德温·福尔(Devin Fore)如此解释“顽固”:“Eigensinn一词的英语意思很多,比如,autonomy(自治)、willfulness(任性)、self-will(自我)以及此处的obstinacy’(顽固)。它在某种程度上暗示顽固而迟钝,不听上级的指示。比如,黑格尔将Eigensinn描述为‘身处奴役之中的自由’。相比之下,克卢格将Eigensinn描述为‘头脑中的游击战’。顽固是历史的阴暗面。……”(第36页)
[31]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伟大继承者,克卢格在此回到由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即,中介散落在人、物、系统之中,他还回到对宿命论的批判传统。德曼德会同意这两个解释。
[32] 参见Rem Koolhaas and Hal Foster, Junkspace with Running Room (London: Notting Hill Editions, 2013).
Writer/editor: 2M2 Art Direction Co.,
Images:©new.qq.com